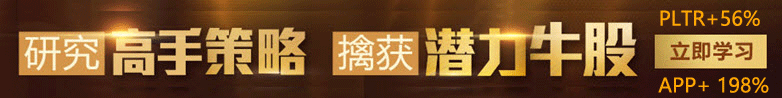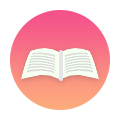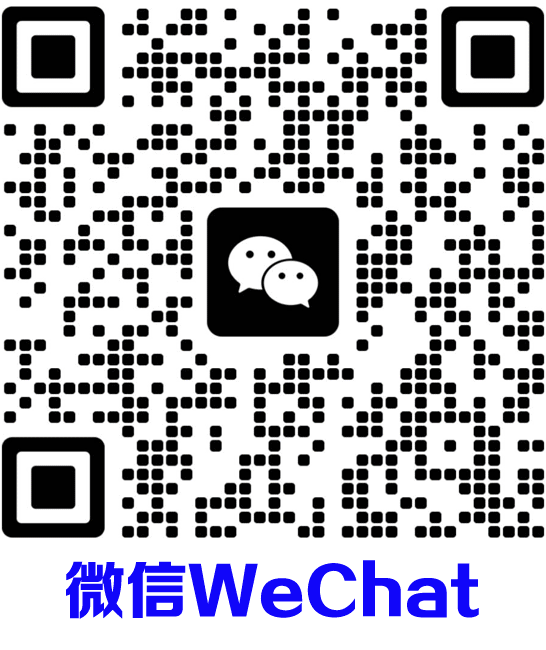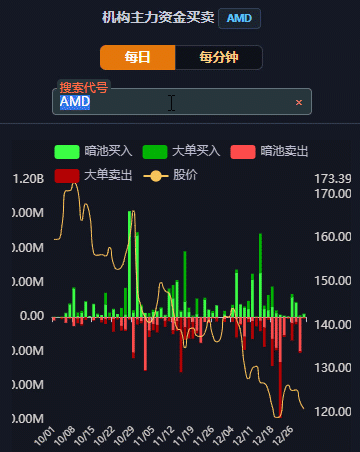1990年代的新疆乌鲁木齐。年幼的赵伊凡,或许还想不到,有朝一日他会成为硅谷最受追捧的创业者之一。他的公司 Notion,估值超过百亿美元,成了无数创作者、工程师、创业者每天赖以组织生活与工作的数字工具。
但在走向这一切之前,他只是一个喜欢画画、热爱设计的孩子。
从西北到北美
赵伊凡出生于乌鲁木齐,小时候就表现出超出同龄人的智慧。在小时候便参加了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。那时,计算机还未像如今这般普及,但赵伊凡却早早地被这个神奇的科技产物吸引。凭借着浓厚的兴趣和极高的天赋,他在小学时就踏上了编程的学习之路。他还学习中国传统水墨画培养了对美学的欣赏。
他自认为已经懂计算机科学后,在多伦多大学选择了认知科学作为主修,同时修习艺术。这听起来像是学术上的“冷门组合”,事实证明,他的这一选择为 Notion 后来的产品哲学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。在 Notion 的开发过程中,他将认知科学的理论与艺术的美学理念相结合,提出了工具不应只是冰冷的程序,而是能 “理解人脑如何思考” 的独特产品哲学。这一哲学理念贯穿于 Notion 的整个设计和开发过程中,使得 Notion 成为了一款深受用户喜爱的数字工具,在众多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。
创业第一课:失败的 Notion 1.0
2013年,他和合伙人 Simon Last 在旧金山创办了 Notion。他们想做的,不是又一款笔记软件,而是一种“像乐高一样”的数字搭建工具。用 block(模块)构建内容,用数据库连接信息流,用简洁的界面让用户自定义他们的工作方式。
最初的 Notion 是失败的。他们在没有明确目标用户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庞杂而不稳定的工具。到 2015 年,融资失败,账户见底,公司濒临解散。
在解雇最后一名同事之后,他们搬去了日本京都。一边节省生活成本,一边重写代码。那段时间里,他们的生活只剩下了编写代码和吃饭睡觉。他们遵循 “侘寂美学” 的极简原则,砍掉 90% 的功能,只保留最核心的 “块(Block)” 概念 ——每个 Block 可以是文字、表格、看板或数据库,用户像搭积木一样自由组合。赵伊凡在笔记本上写下:“Notion 不应是瑞士军刀,而应是瑞士军刀的刀柄 —— 用户自己决定安装什么刀片。”在那里他们也重构理念——Notion 不该“什么都做”,而该是一个能“帮每个人打造自己工具”的平台。
重新崛起逆袭之路
2018 年重新出发的 Notion 2.0,以 “零市场预算” 开启了病毒式传播。以极简设计和强大功能俘获了第一批科技爱好者和创作者。第一位关键用户是独立开发者 Paul Jarvis,他在博客发文《Notion:重新定义我的工作流》,描述自己用 Notion 搭建个人知识库、客户管理系统甚至食谱数据库的体验。Hacker News 上,一条“Notion 是否能替代 Evernote+Trello+Airtable” 的讨论帖获得 2300 + 点赞,程序员们惊叹于它 “用最简单的交互实现无限可能”。
而真正让 Notion 破圈的,是内容创作者群体。作家 Austin Kleon 用 Notion 管理写作素材,将其比作 “数字抽屉柜”;YouTube 博主 Marques Brownlee 在视频中展示用 Notion 规划拍摄脚本,界面上的手绘插图(与亚美尼亚插画师 Roman Muradov 合作)让科技工具多了一份人文温度。到 2020 年,Notion 用户突破 200 万,其中 35% 来自中小企业,他们用 Notion 搭建内部知识库,替代了原本需要 3-5 款软件的复杂系统。
它吸引了大量“新知识工作者”——自由职业者、远程团队、内容创作者。他们用 Notion 写作、建站、做项目管理、甚至整理人生计划。Notion 成了“数字生活的万能胶水”。
此时,赵伊凡的身份已悄然转变:他不仅是一个产品经理,还是全球新一代知识工具哲学的布道者。
东方美学、西方工程
Notion 的收入曲线堪称硅谷奇迹:2019 年 300 万美元,2021 年 3100 万美元,2023 年 2.4 亿美元,2024 年突破 3 亿美元并拥有400 万的用户。更惊人的是用户粘性:70% 的企业用户表示替代了至少 2 款工具,90% 的福布斯云 100 公司在使用。
赵伊凡拒绝将 Notion 定义为 “效率工具”,他在 2023 年罕见接受《连线》采访时说:“当人们用 Notion 规划旅行、记录育儿日记、甚至设计人生目标时,它已经成为思维的外延。就像古人用竹简整理思想,现代人需要的是能随思维生长的数字载体。”
产品界面中,手绘风格的加载动画、可自定义的 “心情模板”、支持 Markdown 与富文本混合的编辑模式,处处体现着 “反科技霸权” 的设计 ——工具不应规定用户如何工作,而应适应每个人独特的思维轨迹。
一位不争而胜的创始人
在硅谷热衷于打造个人 IP 的浪潮中,赵伊凡始终保持低调。他从不参加 TechCrunch Disrupt 演讲,社交媒体账号停更于 2019 年。
唯一一次公开露面是 2022 年在京都举办的 Notion 用户聚会上,他穿着无印良品的亚麻衬衫,用中文夹杂着日语说:“我小时候在新疆看星空,觉得每颗星星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。现在我希望 Notion 是一片星空,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座。”
这种东方哲学式的谦逊,渗透在 Notion 的企业文化中。公司拒绝激进的增长策略,400 万付费用户中,70% 来自自然流量;总部没有豪华办公室,而是在旧金山租下一栋老仓库,员工工位旁摆放着赵伊凡从新疆带来的手工地毯和水墨屏风。当被问及是否担心竞品模仿时,他引用《道德经》:“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—— 真正的壁垒,是对 “工具即人性延伸” 的深刻理解。
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成功时,赵伊凡说,他不认为 Notion 是“成功的终点”,它只是为人类组织思维的工具探索提供了另一种可能。他不喜欢上台演讲,也极少接受采访。但正是在这份安静与克制里,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独特的硅谷故事。
他的存在提醒我们:伟大的工具,不只是效率的体现,也是灵魂的延伸。